编者按:今年来,中国《反垄断法》掷地有声,多家国际巨头遭到重罚。关于这部法律实施的讨论也出现了许多争议,焦点在于:目前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反垄断是限制了竞争还是保护了竞争?在行政垄断未被打破的情况下,反垄断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需要理清《反垄断法》的法理及其施行的目的和意义。对于“中国式反垄断”,听听2014凤凰财经峰会上中国反垄断专家怎么说。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黄勇:“中国式反垄断”已然进入新常态
11月19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黄勇在出席2014凤凰财经峰会时表示,中国《反垄断法》从2008年8月1日施行至今,经历了前三年的“蛰伏期”,近年来才因为一些有影响力的案件发声,随着国内国际对于中国《反垄断法》实施情况的关注度持续加大,“中国式反垄断”已然进入新常态。
黄勇在进一步解释“中国式反垄断”新常态时表示,不同于国外成立专门的反垄断机构,反垄断在我国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三家执法部门把持,是为“中国特色”。
黄勇透露,截至目前上述三家反垄断执法部门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国家发改委查办的案件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都是最大的;商务部主管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所办的案件最多,例如著名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案、P3联盟案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尽管只查办过18起相关案件,却在公开透明、办案专业性和法律程序方面最为出色。
案件逐步“高大上”
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除美国、欧盟之外的,世界上第三大反垄断司法辖区。
黄勇认为,中国反垄断法尽管只有短短的6年多时间,但目前的执法已经进入了一个与美国、欧盟“齐头并进”的新时期。“也就是说,他们(美国、欧盟)所遇到的‘高大上’案子,也就是复杂案件、创新领域的案件,我们同时遇到了。”
据悉,包括目前正在调查的微软案、高通案在内,呈现出来的专业性、技术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对于三家执法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首先是人手不足,相比国外上千人的队伍真是微不足道。”黄勇说。此外,这些案件在我国遭遇的“中国特色”以及中国行政监管模式的不同,又无形中增加了办案难度。
司法审判获进步
尽管如此,黄勇还是呼吁各界不要对《反垄断法》失去信心。
“我们应当看到,随着近年来反垄断案件的查处,除了上述三家执法机构获得了一手的实践经验外,司法审判也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法院已经异军突起。”黄勇说。
业界熟知的3Q大战,即奇虎与腾讯的案件,被黄勇认为是他做出上述结论的强有力论据。“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级别高,最高法副院长出庭,这在中国司法审判史上是很少见的;其次,审判过程中的公开程度、辩论的专业性、网络直播等方面都有目共睹;近8万字的审判结果,法理说明就占了3万字。”黄勇说,该案件的审理,由于真正做到了专业和无歧视,既符合了司法审判的原则、又契合了当下发展阶段特点。
要限制“行政垄断”
作为“中国式反垄断”的一大特色,就是我国在《反垄断法》中专门开辟了一个章节来限制“行政垄断”,即限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一章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
黄勇将日前国家发改委对河北省交通厅歧视性收费进行反垄断调查一案视为向限制“行政垄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法律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怀疑,有人说政府你也罚不了他、政府官员你也撤不了他的职,从这个案子你就可以看到影响力和威慑力非常大。”
因此,黄勇认为,未来深化改革、依法治国,要把防止行业垄断和限制行政垄断并行操作。“《反垄断法》尽管是一部年轻的法律,在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此外,《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给运用《反垄断法》限制“行政垄断”提供了新契机。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一两次输赢不要紧,关键是程序透明
11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2014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国际上反垄断法律从1890年开始至今已在经济学思维方面有了进步,许多当初认为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包括定价、捆绑、最低零售限制这些“听起来不是好词”的行为,今天都有了新的理解。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是重新理解并尊重这种自发形成的商业秩序,然后把本来应该由商人做的决定还给他们,而不是转给一些根本不懂商业的所谓专家和官员。”薛兆丰说。
“柿子就该拣软的捏?”
薛兆丰清楚地记得,1998年5月18日,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的总检察官联合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6项垄断指控中包括捆绑浏览器,薛兆丰当天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种做法。“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们的工商局还在调查微软捆绑浏览器的行为,如果浏览器都不能捆绑的话,现在举目遍地都是违法。真正垄断的不去告,挑一些能够捏得动的软柿子去捏。”薛兆丰说。
彼时,微软捆绑IE被欧盟处以13.5亿美元的罚款。有人曾担忧“微软那么大,如果作恶怎么办?”薛兆丰还曾“天真”地想:微软最大的恶,顶多就是不干了,不干了也不违法吧?
“后来我就觉得自己挺天真的,十几个亿也就是微软两天的收入,就当给反垄断官员和专家小费了。许多企业罚就罚了,也不出来抱怨,认了。”因此,薛兆丰认为,我们应当借此机会重新探讨对反垄断的负面认识。
“证据呢?没人清楚。”
薛兆丰说,《反垄断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1890年至今,《反垄断法》对于垄断的界定,总共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任何勾结、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主体的勾结,抑制贸易和限制贸易就是非法。第二句是:只要是一家的垄断或者企图垄断,就是违法。但是,真正衡量垄断的证据获取却非常困难。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发改委说‘我已经掌握了你违反《反垄断法》的证据’,听起来吓死人,企业就赶快早点拿点钱消灾算了。如果每一家企业都这么想,结果可想而知。”薛兆丰说。
“比如我说我掌握了你偷东西的证据,比如有监控录像、有证人、有赃物,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你说你掌握了违反《反垄断法》的证据,世界上没有人清楚。”
因此,薛兆丰认为,《反垄断法》重点在于如何解释。“许多商业行为,哪怕在美国是违法的,但还是不能阻止。比如厂商让下面的经销商保持一定价格,不要在价格上竞争,这是非常常见的。”
“一两次输赢不要紧”
针对目前热议的反垄断与贸易保护的关系,薛兆丰认为贸易保护不在于保护本身,而是在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以及这样做的目的。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体起源的国家,“中国式反垄断”是不是会变成“不反国有、专反私有”,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反垄断法》出台后,不少专家学者号召学习美国。但薛兆丰强调的是,美国在反垄断方面也走过弯路,也做出过很多愚蠢的判断,美国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程序透明。
“法官怎么想的、证据是怎么理解的,案件的始末、事实、思考的过程、思考所用的理论框架、反对意见,都清清楚楚地写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案子在美国可以读个50年甚至上百年,随着认识的不断改进,标准程序就出来了。一两次的输赢不要紧,程序的公开透明、开放、标准化才更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朱海就:《反垄断法》本身就很可笑
11月19日,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朱海就在2014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从经济学角度说,市场天生就是垄断的,“因为每个企业总是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个行业具有独到优势的企业”。
因此,朱海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竞争和垄断可视为同义词。“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只有垄断了你才能在市场立足,政府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垄断,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垄断。”
按照朱海就的观点,垄断还是一个信息判断的问题。“政府无从判断企业究竟是损害了市场还是帮助了市场,也无法判断企业有没有损害消费者,只有市场和消费者自己才能做出判断。”因此,他认为,《反垄断法》本身就很可笑,根本就不应该有,而是应该限制政府权力。“现在《反垄断法》变成了政府扩大权力的工具了,政府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市场秩序,而不应该把法律变成工具来使用。”
朱海就认为,反垄断是一个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判断。反垄断官员容易有“反垄断是最优法律结构”的想法,但实际上这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
朱海就反对任何将《反垄断法》国家化的意图,“理论上法律不应该有国家色彩,如果站在世界公平角度理解法律,比如某个企业倾销,实际上对消费者有利,为什么就认为一定是不好的呢?经济学上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商家可以自主定价。”
针对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问题,朱海就认为一个企业不可能完全凭借知识产权获益。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保护,也是企业的市场策略问题,完全属于企业自主行为。“如果这个企业不能保护它的知识产权,说明企业技术能力缺乏、说明它的知识产权不完整。知识产权确实会被别的企业模仿,但是模仿不一定就能成功,还需要许多其它条件,比如营销、管理等。”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政府总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
11月19日,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在2014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随着兼并重组过程中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确实会出现反垄断案件增多的现象,反垄断执法是政府层面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执法手段。
管清友认为,过去我国在产业政策方面管得太多太死,“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也吃过很多亏,光伏产业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未来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
管清友表示,反垄断执法要直面一个如何对待石油公司、移动、电信等“大块头”的问题,“你说反这个反那个,如果这些产业上游都没有动过,恐怕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反垄断。比如三桶油,政府就规定了中石油管北边、中石化管南边,中海油管海上,这是不是垄断?如何去打破?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大的体制结构调整,恐怕不是一个反垄断法能解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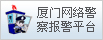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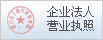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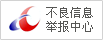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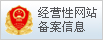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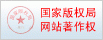

 在线客服1号
在线客服1号 扫一扫微信咨询
扫一扫微信咨询